我们的声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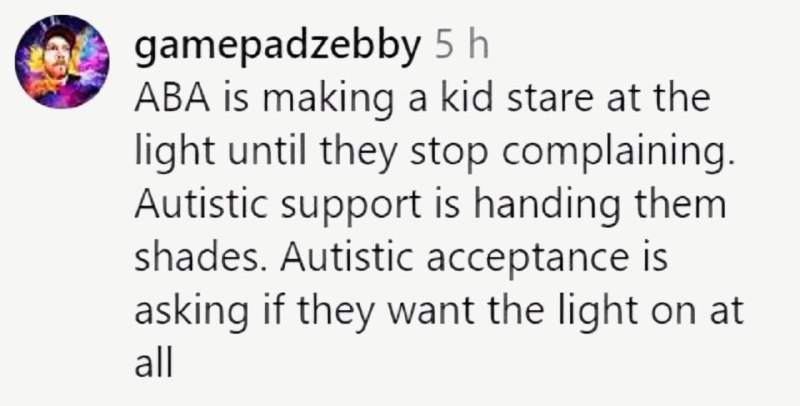
关于自闭谱系孩子的复建,很多家长会送孩子去参加“应用行为分析治疗/ABA行为治疗”。但实际上,这种所谓的“治疗”常常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精神创伤。孩子看上去“更听话了”,但实际上却是在受到反复高压“训练”后表现出的刻板行为。在自闭谱系人的社群里,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讲述这种“疗法”给自己带来的噩梦般的经历。
“所谓的应用行为分析治疗/ABA行为治疗,更像是让自闭谱系孩子看向光源,直到孩子不敢抱怨。真正的对自闭谱系支持应当是给孩子提供帮助,让孩子在不得不接触可能触发感官过载的光源时有所遮挡,而接纳自闭谱系人和自闭谱系孩子,意味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,应当询问对方是否有引发感官过载的光源,并为对方关掉或移除那些光源。” source

作为一个不符合所谓的“性别规范”的小孩的经历,和作为一个神经多元(自闭谱系、注意力障碍、阅读障碍等)小孩的经历,其实是非常相似的。你无法到达那些大人们的“期待”,然后大人们认为自己必须“纠正”你,哪怕你根本就不想被纠正。家长对你失望,然后对你大发脾气,问你“为什么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”。你心里有很多很多感受,但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在你说,“你感受的不对”。
小时候的我只能一直卑微地尝试,尝试去迎合大家的要求,这样就可以让大家不要对我生气,不要拒绝我排挤我。然后我几乎花了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整整十年去走出这个怪圈,放下别人的期待,去探索自己究竟是谁。幸运的是,我找到了我自己。不是所有人都有我这样的幸运。
很多人会讨论,“当小女孩表现出男性气质的时候,她是会被惩罚,还是会被奖励?” 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好问题。因为真相是,一个小孩会被奖励还是惩罚,完全取决于大人的期待。
而所谓的“传统性别观念/传统性别理论/传统性别意识形态”,让大人们在知道小孩性别的那一刻就开始塑造自己对孩子的期待了。自从有了超声技术之后,这个期待甚至早于孩子的出生。在我的家乡,大人们听到孩子是男孩消息常常会说,“太好了!他以后会踢足球!” 而那些还在肚子里的女孩子们,无论她们踢得多么用力,都不会有人想到足球。
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长无法接受孩子是跨性别的原因。因为这和原来的期待相差太远了。但说实话,很多时候,孩子从来都不是家长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可惜的是,不少家长根本看不到Ta们真实的孩子。当你和你的家长说你是跨性别的时候,家长们听到的是,你杀死了Ta们心中的一直爱着的那个想象中的孩子,然后用真实的你自己取而代之了。
真相是残酷的。你的家长很可能宁愿要那个自己想象中的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孩子,而不要你。在Ta们心中,你是那个冒牌货,你杀死了那个“真实的小孩”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民间的说法里,自闭谱系的孩子是被精灵掉了包,偷走了“灵魂”的“假小孩”。
我写的这些,是受到娜奥米·克莱恩写的《分身政治》里的说法启发的。那本书很好,激发了我很多的思考。在那本书中,克莱恩主要分析了自闭谱系的小孩如何受到父母的期待的影响。但我觉得她的理论也能解释各种跨性别相关的经历。
我们可以想象,跨性别的经历就好像是你有一个影子。人们认为那个“影子”才是真正的你。当你和别人解释想象中的那个“影子”并不是你的时候,有人会尝试去理解,也有人不会。那些不理解的人会面朝着你,然后选择完全无视你,而是看向自己心中的那个你的“影子”。这真的会让人很难受。但最可怕的是,有些人会认为你是冒名顶替的“假人”,因此会攻击你,企图让那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“影子”回来。这些人沉浸在自己内心虚幻认知之中,认定你是“说谎精”,认定你操控了那个从没有存在过的“真实的人”,认定你不怀好意...
https://www.tumblr.com/shamebats/770413358503575552/klein-talks-about-children-as-doppelgangers-made

如果你在人行道上迎面遇到一个使用轮椅的人,请尽量向外侧避让,把里侧通常更平整的路面让给那位使用轮椅的人,因为:
❶ 靠近外侧的路面容易颠簸,轮椅的使用者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保持直线行驶。手动轮椅的使用者常常因此汗流浃背。
❷ 坐在轮椅上的人有时难以看清轮椅离路沿还有多少距离,在使用人行道的外侧时比较容易意外跌入车流,造成危险。而且如果电动轮椅翻倒的话,需要几个人一起才能将沉重的轮椅扶正,救援有一定难度。
另外,如果在公园或小区的路上迎面遇到使用轮椅的人,请看一下路面的情况,尽量把更平整的路面让给使用轮椅的人。如果道路很窄的话,您可能需要避让到草地上。 source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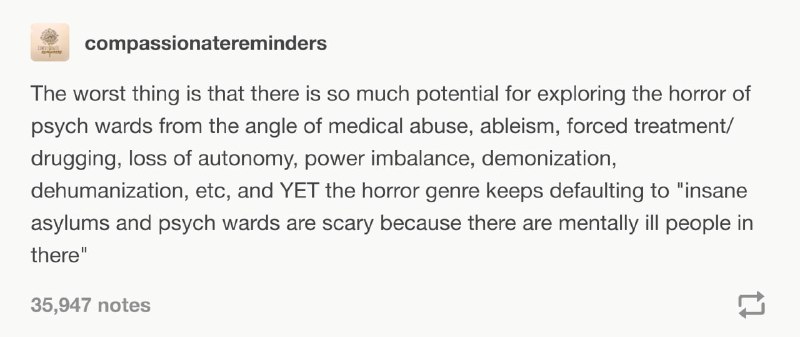
明明精神病院题材的恐怖作品有很多很多角度可以切入,包括医务人员对病人的虐待、医院违背病人意愿的强迫治疗和强迫服药、病人人身自由和自主权的丧失、病人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力不平等、社会和医院对精神病人的不公、将病人被妖魔化、不把病人当人看,等等等等;
但不幸的是,绝大多数作者还是选择继续是去重复社会里那种“精神病人很恐怖所以精神病院很恐怖”的误解和歧视作为作品“底层恐怖逻辑”... source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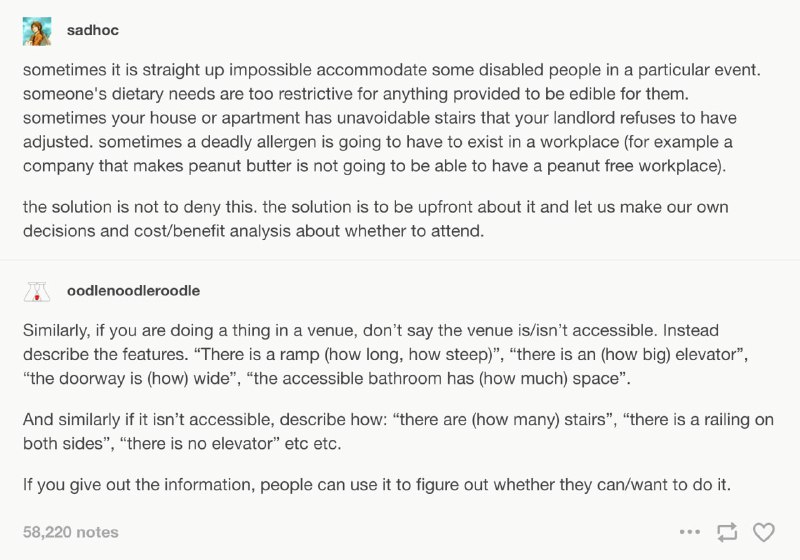
我理解,有些时候确实很难照顾到所有身心障碍相关的需求。也许是有人饮食上的限制太多,以至于很难安排好这个人的餐点。也许是活动场地安排在了你的家里,但你家大楼没有电梯。也许是花生酱工厂要招工,无法招那些对花生严重过敏的人。
我希望在这种场合下,主办方可以写清楚自己这边的情况,让我们有身心障碍的人自己决定到底要不要来。不要只写“身心障碍友好”或者“不设有身心障碍友好措施”,而是写清楚,“有多长多宽倾斜角度是多少的坡道”、“有大电梯/小电梯/没有电梯”、“入口宽度是多少”、“障碍友好的厕所是大是小”,“必须要走几阶楼梯/楼梯有无扶手”,等等等等。 source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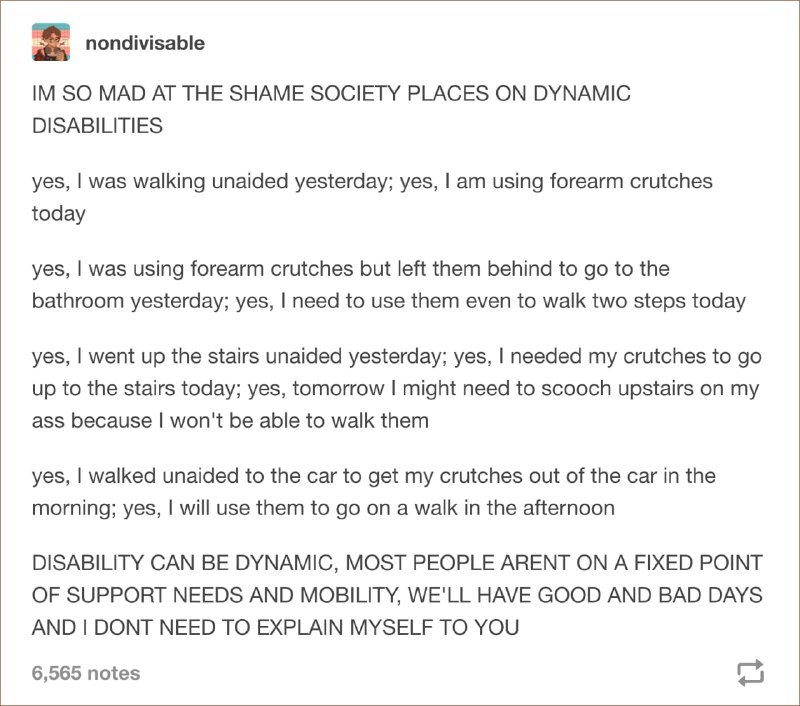
社会总是嘲弄和诋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程度起伏波动的人。
也许我昨天可以不借助任何器械行走,但今天需要拄上拐杖才行。
也许我昨天可以放下拐杖去上厕所,回来再继续拄上拐杖,但今天做不到。
也许我昨天可以不借助任何器械上楼梯,但今天非得用拐杖才能上楼。
也许我早上还可以不借助任何器械走到车上,把我的拐杖从车里拿出来,但我这么做,恰恰是因为我知道到了下午的时候,我非得拄上拐杖才能走路。
身心障碍程度是会起伏波动的。我们的需求和行动能力是会常常变化的。有些日子对我们来说会更容易一些,有些日子对我们来说会更困难一些。不要因此质疑我们“没病装病”,打探甚至强行要求我们公开我们私人健康状况的细节。 source
](/media/attachments/lif/life_with_disabilities/2028.jpg)
不是所有的身心障碍都可以被一眼看出来的 source
